西安人都注册了,还不快来?
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,没有账号?注册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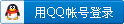

×
日记 过大年居家轮流吃大户的往事【严建设】 2024年01月31日 Wednesday阴转小雨


那天我的初恋女友小慧的闺蜜段灵和其丈夫赵尔强来找过我,说想买一台便宜的照相机。我答应送她一台,然后次日去大车家巷她家,送的是华山AE电子照相机。并索要当年我的老照片,是我送她的。我保存的被小慧不讲理撕碎了。段灵惊讶地说,原来你一直想着她。老照片她答应还给我,若想保存的话,翻拍也成。但一直没还。她是约莫50年前唯一和我共享那份羞悦秘密以及怅惘痛苦的人。然后赵尔强回家摆弄照相机,并合伙包萝卜羊肉饺子吃了,喝了几盅绵竹大曲。次日其儿子赵时来我家,说是舅舅给他改好了一首诗拿来,说他妈说的,叫我托个人推荐到西安晚报社发表。那次也是我唯一在她家吃的一顿饭。当年那台照相机也就一般人两三月的工资。


这种轮流坐庄吃大户的现象,实则是一种传统的社交活动,尤其在中国的农村地区更为常见。在过去,由于人们的经济条件有限,这种轮流坐庄的方式可以让大家都能享受到一顿丰盛的酒肴饭菜,同时也能增进彼此之间的友谊和感情。 在这个过程中,大家轮流做东,在自己家里款待其他朋友,准备丰盛的酒菜,一起聊天、打牌、唱歌,热热闹闹地度过一个愉快的晚上。这种方式既能让每个人都享受到美食和欢乐,又能节省开支,是一种非常实在的社交方式。 由于我住的距城区颇近,则经常有朋友同学来串门。绝大部分西安人过去都很穷,按风俗习惯,若不是约定,随意来串门的客一般是不招待吃饭。但一般会礼让再三:你吃了么,嫑客气就在咱家一搭吃吧。陕西此地俗话说:让人是个礼锅里莫下米。说归说,心里根本没请人吃饭的意思。顺嘴说句客套话而已。彼此都心照不宣。 1983年,我住东壕村,对待来客非常高兴,总是想方设法搞些酒菜招待一番。这也是妻子沿袭了岳父为人做事的习惯、我沿袭了上山下乡插队时的习惯。当然没钱,只得搞些很便宜的酒菜。我一般会骑自行车到和平路胜利饭店,在饭店隔壁当年有一家李家村食堂的小饭馆,买点酒菜。 我会捡便宜的买,丹凤红葡萄酒0.68元/瓶,散啤酒0.18元/斤,熟猪头肉0.68元/斤,还有一种很便宜的熟猪肝,不是我们现在吃的猪肝,当年叫做沙干,口感有点面的才0.38元/斤。回家后再剥一头大蒜,拍几根黄瓜、切些萝卜丝装碟上桌,搞个西红柿炒蛋,再挖两碗白面,在村里压面机房换点切面煮煮,就能招待人了。家里只有俩折叠椅,一张折叠桌。有个铺着桌布的大木箱,借床沿凑合坐坐。再不然去隔壁邻居家借凳子。 这样有几位朋友成了常客,经常赶饭口来串门,对于我俩小两口来说也是负担。好在一位常来的朋友,也是我的发小老同学名叫高潮的,食素的不吃肉。散啤酒盛在铝锅里,再装进网篮中,我单手撒把骑自行车带回家还是冰的。 有个夏夜,妻子出差我独自在家。女儿照例送去奶奶家。这样来的朋友饮酒很晚,有人就住在家里了。那次有位独居的美女邻居,就住在隔壁,芳名叫做马莉,当年在文艺路一带做布匹生意。平常也没啥来往。 当天晚上她来家借娃娃书,看到我家来人饮酒,转身回去,不大一会送来一只油炸烧鸡。我们非常高兴。但切开我尝过后,感觉可能是天气太热已变味了,怪不得用煤油炉子油炸一下。但来串门的朋友不管不顾我的一再提醒,照例一顿大嚼,竟就着散啤酒,把那只坏烧鸡咔嚓喀嚓吃得精光。也可见当年食物匮乏程度。那朋友也是我的老同学,名叫李海滨。是东壕村的上门女婿。 也有个别豪爽的朋友。有两位朋友也来混饭。但常带点食物过来。一位是国家地震局的叫做史广军、一位是肉联厂的叫做李福祥。外号叫做孬。 198-9年的时候,当时社会上比较混乱,我也没法做生意,就在家里闲了两三年。当年已住到东县门的教委家属院里了。因那地方就在城区里边,周边东大街、东羊市、和平路、马场子、饮马池、菊花园、东号巷都离得很近,抬脚就到,地理优势很好。所以牵连不断的有些人老来家里打麻将,唱歌,看录像、吃饭喝酒聊天。 那些年每天家里都会来一些朋友。有时候也就三五个人,有时候七八个十几个,最多的一次是过年,呼啦一下来过30多个人拜年。来的人呢,都得吃饭。当时我和妻子就在家里招待他们,无非也就是些鸡鸭鱼肉。有时候买点现成的卤味回家,做的最多的是回锅肉、酸菜鱼、清蒸草鱼、辣子鸡、糖醋排骨。坐不下拉过沙发,扶手上挤着凑合。 当年有人给我送来的茅台酒五粮液都喝光了,小后院花园里的酒瓶子堆积如山,买啤酒像青岛啤酒、汉斯啤酒不是一瓶两瓶,每次都是提两捆三捆。用尼龙捆绑绳一捆是9瓶。感觉待客很高兴。座上客常满,杯中酒不空。 当年家里来的客人也比较紊杂,有的是朋友,有的是亲戚,有的是亲戚的朋友,有的是朋友的朋友,还有朋友的朋友的朋友,就像阿凡提故事里说的那样,我们应接不暇。 慢慢的生出事端来,有的人要借东西,借钱。借的最多的是稀罕的花带,有家陕报社的记者头次来家,酒后借走了一书包十几盘,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他。都是刘备借荆州一借不还。借钱后玩失踪,次日后再也不见人影,几十年了。前文曽叙。 吃饭实际上也不讲究。但有时候很讲究。 记得有一次。有个名叫郭长安的小兄弟带了一位朋友来,说是叫做张立。是西关桃李春烹饪学校的业务校长,名头很大,曾在联合国给贵宾们做过饭。所以请他来做饭。他做的饭呢,摆盘看相好,但是很费油,浪费掉很多油。味道比较清淡。味精、胡椒粉用的重,不用五香粉,用牛奶。还得叫我差人去买从来没买过的黄油。 胃口最好最能吃的是张宁。其喜欢古典文学,一手好字,诗词歌赋无所不通。算是高干子弟吧,当年也是几乎每天都要来的。 当年几乎每天都要来的人有郭长安、丁锡山、王晓钧、徐松涛、康小荣、张宁、高潮、李海滨、李西茂以及贾宁等十余人。也都是牌友,主要是来混饭打通宵麻将的。有的家伙住处距我家很近。走路几分钟可到,所以几乎天天来家。如丁锡山、高潮、康小荣。 当时我们家的安全门是从店里边拆下来的铁栅栏门。有时回家打开手掌般大的铁锁子一看,栅栏门的缝隙里被人塞进了报纸卷。打开一看,有时候是一条猪腿,有时候是一大包排骨,有时候是一大包猪腰子。有时候是一大包猪蹄子。这些东西主要是肉联厂的李福祥送来的。也有是姚村机场屠宰场附近工作的朱广财送来的。 我告诉李福祥,你们工资低,赚俩钱不容易,不要乱花钱。他说花什么钱?一分钱都不花,这些东西都是在附近副食商场、肉铺里拿的,他们在我肉联厂进货,紧俏货都得我给他们预留。再说我磅秤上随便秤砣高一点,就啥都有了。 这样几年下来,我们两口子光出不进,渐渐地的有些后手不接经济上捉襟见肘了。饭菜质量就稍有下降。为了招待来客,我卖掉了一些自己的收藏品。比方字画、邮票。一张猴方联邮票,当年我去北院门邮社只卖掉了850块钱,因为急着用钱。现在好像是四五万块了。当年为招待人,卖掉了大量的邮票。整版的杜鹃花、整沓的三国小型张。还卖掉了整套的清朝邮票红印花,只卖了4700块钱。现在的价格应该在100多万了。 再后来手头紧了,家里频繁不断来人还得请吃饭,就去回坊买很多煮熟的牛下水冻在冰箱,来客切凉盘、加白菜豆腐等做大烩菜。牛肝牛肠牛肚牛头肉,都便宜得很。 当年卤味好吃的是朱秀英梆梆肉,当年熏肠熏肚每斤十几块钱,熏头肉熏肺便宜。但有些人还计较得很。发牢骚说就给人吃这?咋别人来了大鱼大肉上呢。此话是有位叫薛武奎的老同学说的。他一直崇尚清炖肘子黄焖鸡,黎明的瞌睡半路的妻,是口头禅。 那次他和叶经天来家吃饭。我买了3斤梆梆肉,拍了几根黄瓜用剑南春招待他俩。多说一句,自从他进城以后,那段时间积年累月常来我家混饭打牌,但从没回请我吃过一次,哪怕。而那次买梆梆肉的钱,也是我卖邮票的钱。当年的梆梆肉算是熟食中贵的。现在也贵。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,人们的经济条件逐渐改善,这种轮流坐庄的方式也逐渐被更加现代化的社交方式所取代。现在居家请客者稍,大都是在酒店餐厅请客。但对于很多人来说,这种传统的社交方式仍然是一种难忘的回忆,是人们之间友谊和感情的一种独特表达方式。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,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交习惯也在不断变化。在80年代末、90年代初,城市和乡村确实流行过“轮流居家坐庄吃大户”的状态,这是一种基于社区或家庭之间的轮流做东、互相宴请的习俗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,这种习俗可能逐渐减少或消失,这可能是由于多种原因。生活节奏加快、社交方式的改变、经济条件的变化等等。 虽说这种习俗在现代社会可能已不那么普遍,但并不意味着它已完全消失。在一些地区或社群中,可能仍保留着类似的习俗。此外,现代社会中仍然存在着各种形式的社交活动和聚会,以满足人们交流和互动的需求。
| 
 秦岭山上分水岭上摆摊的人多了2161 人气#图说西安
秦岭山上分水岭上摆摊的人多了2161 人气#图说西安![[散文]蛇皮袋子里的称](https://img.ixian.cn/attachment/block/4a/4ac74bd33a9f1253808302ba4b966cb1.jpg) [散文]蛇皮袋子里的称742 人气#古城杂谈
[散文]蛇皮袋子里的称742 人气#古城杂谈 陕甘宁高铁梦8701 人气#城市发展
陕甘宁高铁梦8701 人气#城市发展 突发奇想: 如果在陕西和山西之间有个大湖5871 人气#古城杂谈
突发奇想: 如果在陕西和山西之间有个大湖5871 人气#古城杂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