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安人都注册了,还不快来?
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,没有账号?注册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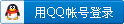

×
“问君归期未有期,巴山夜雨涨秋池。何当共剪西窗烛,却话巴山夜雨时。” 一场绵绵不绝的梅雨,使这岁炎热的夏天陡然爽凉。黎明前夜,听着细雨霏霏拍打窗棂的声音,梦回李商隐诗句,已然毫无睡意,索性起床打开手机,是孩儿夜半发来的“已到”短信。孩儿结束两个月的假期,于昨天乘车西去开始又一个大学的生活,我是既感高兴又感惆怅,高兴的是孩子的成长,知道双亲的担心和不忍午夜的扰休,惆怅的是大学毕业未见长进,还是那样懵懂单纯,做父亲的内心是如此杂陈无表。 看过高尔基《我的大学》,也见过时下大学生活,那么我的大学呢? 如果以围墙论,我确然没有大学晨钟暮鼓般的体练。早年西安三年的学习生活不过是另类的中学生活而已,学校保姆式教育造就了一个有着癔想症“洋人”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遵重知识遵重人才的大环境下,我等被强勉划入知识分子,就自以为是很有文化,不知天高地厚目空一切,翘首以待。社会大学的教育,使我深感大脑的弱智,知识的贫乏,思想的愚昧,在高悬头颅的背后是深深的自卑。我是知识分子吗?我是有用人才? 诚然,上世纪七十年代末,对于一个出身农家,半农半读,越过秦岭,走出大山,成为省城学子撼为一大幸事,而先天教育不足,乌到骨子里农人本性也使我见人矮三分,即使在城里生活三十多年的今天还是本性不改,只不过现在我可以神清气爽以农夫自居而不觉得卑微。 学医不是我的兴趣,也非所愿,就如时下很多高考生被父母安排志愿一样。学医好就业,社会怎么变,医生有饭吃,如此稀里糊涂去上学,毕业后既不能救死也不能扶伤,还被家人戏称为假医生。这样的尴尬处境,内心的彷徨是多么地强烈啊!因而闲暇之时,学些舞文弄墨的东西排遣心中的郁闷,在地方小报上发些小诗、散文什么的豆腐块聊以自慰。不过害怕被领导批评为不务正业而偷偷地投稿。记得第一次在安康日报副刊发了一首小诗是一九八六年,笔名程黎是也。一九八七年参加河南一家杂志社组织的全国小小说大奖赛,以小说《乳房》夺得了三等奖,五十元奖金喊了一邦哥们举杯狂饮,喝得烂醉如泥。 一九八四年贾平凹先生来旬讲学,憨厚的先生讲的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——人是要有野心的,文学创作也不例外。搞点文学,总得有些积累,阅读名著是不可少的准备,虽谈不上厚积薄发,文学素养这个功课做足是不会错的。那时,图书馆在老城,新华书店也在老城,星期天经常光顾书馆书店,读了一些杂七杂八似懂非懂的书,无甚长进。八七年参加汉语言文学大学自考,惭愧的是考了两年贻人口实,只有外国文学和写作两门过关,所幸的是对外国文学有些一似而非的了解……如乔伊斯《尤里西斯》、普鲁斯特《忆流水年华》、马尔克斯《百年孤独》等。 说起《百年孤独》一书,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安康新华书店化了五元钱买了一本,也许天资愚钝,我并没有读懂,到现在只依稀记得布恩蒂亚家族在马孔多镇繁衍了七代,生出来一个长尾巴的婴孩;奥雷连诺上校译完羊皮手稿瞬间马孔多孤独不再。 玩文学,不仅要精练语言,究习技巧,更重要的是入世的洞察把握,出世的深邃卓见,如哲人般的睿智爬行,成大智慧者。有感于此,八九年受友人鼓惑,入中国社会学函授大学社会学专业学习两年取得毕业证书,习得一点观察社会的方法,权为我的大学吧。 张纪满2017-09-09
| 
 乘地铁是看手机的好时机704 人气#图说西安
乘地铁是看手机的好时机704 人气#图说西安 雨中漫步古城墙根1319 人气#图说西安
雨中漫步古城墙根1319 人气#图说西安 在西安,反扒能手被返聘了2172 人气#古城杂谈
在西安,反扒能手被返聘了2172 人气#古城杂谈 一切都是缘分,不要恨,不要计较,不要难过667 人气#古城杂谈
一切都是缘分,不要恨,不要计较,不要难过667 人气#古城杂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