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安人都注册了,还不快来?
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,没有账号?注册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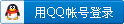

×
本帖最后由 司马君 于 2025-10-11 20:31 编辑
王宝钏与薛平贵的爱情故事,这俗套得像是从哪个话本子里直接扒下来的——英雄救美。
长安街市,人潮熙攘,她的车驾受了惊,马儿扬起前蹄的混乱里,一个衣衫虽旧、眉眼却亮的青年攥住了缰绳,制止了一场可能发生的横祸。
他叫薛平贵。她是相府千金王宝钏。目光相接的一瞬,她心里那点被规矩框住的东西,似乎"咯噔"一声,裂了道缝。
她知道父亲王允绝不会点头。一个穷猎户,想做相府东床?简直是笑话。可她很执拗,偏不。
几日后,那场轰动全城的抛绣球,明面上是天意择婿,暗地里,是她精心策划排演的一出大戏。
绣楼之下,人头攒动,她目光掠过那些翘首以盼的贵胄子弟,精准地找到那个企盼的身影。
然后,绸缎扎就的彩球被轻轻的跑向长空,划过一道美丽的弧线,不偏不倚,落入他怀中。
她站在高处,看着他惊愕又狂喜地接住,心里漫上的,一半是得逞的甜,一半是决绝的涩。
父亲的震怒如山崩海啸。"你若执意嫁他,便不再是我王允的女儿!"话语像淬了冰的刀子。
她跪在厅前,背挺得笔直,卸下珠钗,脱下锦缎,只穿着一身素布衣裙,在满堂或惊或鄙的目光中,一步一步,走出了那座朱门深宅。
那一刻,她觉得自己是为爱献祭的勇士,悲壮而又纯粹。
新婚的"家",是城南郊一孔废弃的寒窑。
蛛网在墙角结着灰蒙蒙的梦,土炕冷硬,四壁空空。从前,指尖拈的是香茗细点,如今,操持的是粗粝炊烟。
她学着挑水,肩膀磨得红肿;她咽下以往绝不会入口的食物,味道陌生得像在咀嚼另一种人生。
薛平贵起初是愧疚的,拥着她反复说着"委屈你了",誓言灼热,承诺着看不见的未来。
这窑洞虽破,夜里倒能看见比相府庭院里更密的星星。
她靠着那点誓言和星子的微光,竟也从清贫里咂摸出一点名为"爱情"的虚假甜味。
然后,朝廷征讨西凉的檄文就下来了。建功立业的机会仿佛天赐,他眼里的火苗被点燃了。
他说:"宝钏,你等我,我必挣得功名,风风光光接你离开这里。"
她看着他,心里有千万个不舍与担忧,却还是点了点头。她不能折断他的翅膀,她得做他"懂事"的妻。
送他出窑洞的那天,风很大,吹得她单薄的衣衫猎猎作响。
她站在坡上,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尘土飞扬的路尽头,成了她十八年守望里,最初也是唯一清晰的定格。
日子,是被拉长了的,重复的苦涩。
春天,她去挖野菜,指甲缝里塞满泥垢;冬天,她瑟缩在窑洞深处,听着北风的呼啸,一遍遍回想他掌心的温度。
一年,两年……十年……镜子里的人,皮肤粗糙了,眉眼被愁苦刻上了细纹。
那点"爱情"的甜味早已在日复一日的等待中消耗殆尽,只剩下一种近乎本能的惯性,支撑着她日复一日地望向那条他离开的路。
偶尔有消息零星传来,像投入死水里的石子,却激不起多少涟漪。
有人说他立了功,有人说他受了伤,还有更不堪的,隐约提及西凉公主……
她总是用力摇头,把这些"谣言"甩出去。她不能信,信了,这十八年的坚持就成了笑话。
直到那个傍晚,夕阳把土坡染得一片惨淡。
她正弯腰,费力地掘着一丛特别粗硬的野菜根。这时,走过来一个曾经在军中待过、流落至此的蓬头垢面的老兵。
老兵嚼着草根,含混不清地说:"……薛平贵?早他娘的在西凉当上驸马爷啦!锦衣玉食,儿女都能跑马了,谁还记得这穷地方……"
"驸马爷"三个字,像一道终于劈下来的闪电,瞬间照亮了她十八年蒙昧的坚守。
她僵在那里,手里还攥着那根沾满泥土的野菜,冰冷的触感从指尖蔓延到心里。
原来不是战死沙场,不是身不由己。
是另娶新欢,是锦衣玉食,是儿女绕膝。
她慢慢地、慢慢地直起酸疼的腰,望着天边那轮将沉的、血红的落日。
寒窑里还堆着她准备过冬的、晒干了的野菜,那苦涩的气味几乎浸透了这十八年的每一寸呼吸。
她忽然低低地笑了起来,笑声干涩,像风吹过破瓦。
"薛平贵,"她对着空无一人的窑洞开口,声音平静得可怕,"我王宝钏用十八年,才嚼碎了'情义'这两个字。
它们和这野菜一样,初尝是苦,回味是涩,最后只剩下扎破喉咙的疼。"
她松开手,那根被攥得变形的野菜掉在地上。
"你欠我的,早已不是荣华富贵,而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交代,一个让我这十八年不至于像个彻头彻尾笑话的结局。"
后来,他果真回来了。
旌旗仪仗,煊赫威武。
他已不是那个离去的贫寒少年,而是西凉的王。
他站在那孔破窑前,锦衣华服与周遭的破败格格不入。
他看着她,眼中或许有片刻的恍惚,随即涌上的是她看不懂的复杂情绪,有愧疚,有审视,或许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如释重负。
他向她伸出手,声音带着刻意放缓的温和,诉说着当年的"不得已",描绘着未来的"荣华"与"补偿"。
王宝钏没有动,只是静静地看着他,看着这个在她记忆里鲜活、在现实中却已陌生的男人。
他那些精心准备的说辞,在她十八年的风霜面前,显得如此苍白可笑。
等他终于说完,空气中只剩下难堪的寂静。
她这才往前迈了一小步,目光清凌凌地落在他身上,轻轻问了一句:
"十八年,陛下可曾有一梦,梦见过这窑洞里野菜的滋味?"
一句话,像一根冰冷的针,猝不及防地刺破所有精心粉饰的平静。
薛平贵伸出的手僵在半空,脸上的表情瞬间冻结。
那些准备好的封后诏书、珠宝赏赐,在这一句轻飘飘的问话前,突然变得毫无重量,甚至滑稽起来。
它剥开了所有虚伪的补偿与追封,让那段被牺牲、被遗忘的岁月,露出了血淋淋的底色。
那根断裂的野菜,静静地躺在泥土上,像是一场豪赌输了后躺在地上的筹码,又像是无耻文人唱完赞歌后扔下的秃笔。
原来,这不是爱情,只是一场长达十八年的、清醒的凌迟。
2023年5月写于西安 图片来自AI制作
| 
 好家伙赛格电脑城闭店还有仪式!人还挺多的4666 人气#古城杂谈
好家伙赛格电脑城闭店还有仪式!人还挺多的4666 人气#古城杂谈 有这么写法?3297 人气#古城杂谈
有这么写法?3297 人气#古城杂谈 西安“最豪华妇产医院”因无人出价而流拍!4064 人气#城市发展
西安“最豪华妇产医院”因无人出价而流拍!4064 人气#城市发展 「2025度小满西安马拉松赛」奖牌、参赛服公2043 人气#古城杂谈
「2025度小满西安马拉松赛」奖牌、参赛服公2043 人气#古城杂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