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安人都注册了,还不快来?
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,没有账号?注册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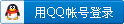

×
出身于社会底层的家庭,成长中目之所及多是谋生的艰辛与尊严的脆弱。我曾见过街边小贩为躲城管推车狂奔的慌张,也听过邻家夫妇因几块钱水电费而爆发的争吵,更目睹过同行摊贩为争抢地盘而相互诋毁的无奈。这些碎片逐渐拼凑出一个早熟的认知:生活对许多人而言本已不易,何苦再彼此为难?
这份体会,在十九岁那年的夏天变得具体而锋利。当年九月,我收到警校录取通知书,需在一周内办妥粮食关系转移与户口迁移。派出所的手续办得出奇顺利——接待我的警官正是警校校友,他眉眼含笑,耐心指点,最后拍拍我的肩说:“师弟,未来看你的了。”那一刻,掌心的温度几乎让我错觉:这个世界或许本就如此友善。
错觉在第二天清晨破碎。天未亮,我和父亲便拉着架子车出发,车上的粮袋压出深深辙痕。到达粮站时,太阳已爬上粮库灰白的墙壁。管库员抬抬下巴:“先验粮,再称重。”我小跑至办公楼二楼,找到质检室。门虚掩着,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人斜靠着椅背抽烟,烟雾缭绕中正与人谈笑。我轻声说明来意,他眼皮未抬:“先去上风车。”
我只好返回,与父亲一起将上百斤粮袋抬上风车台。手摇转柄吱呀作响,链条带动扇叶,麦粒如金色瀑布泻下,秕壳与尘土被吹散。晨光中飞舞的,仿佛不是尘屑,而是我们小心翼翼捧着的希望。重新装袋后,我再度上楼请他。这次他慢悠悠起身,趿着布鞋来到粮库,伸手插进粮袋,抓起一把麦粒——颗粒饱满,在阳光下泛着琥珀光泽。他却只看了一眼,便在质检单上刷刷写下“三级”。
父亲接过单子,手指微微发颤:“同志,这麦子……咋才是三级?”那质检员嘴角一撇,弹掉烟灰:“最后一回卖粮了,还挑剔啥?这会儿再不压你们的级,往后可没机会了。”说完转身离去,布鞋拖过水泥地,沙沙声像钝刀划过心头。父亲没再说话,只是望着他背影,然后默默把质检单折好,塞进衣袋。那个动作很轻,却在我心里砸出沉重的回响。
多年后,我见过更多面孔:有窗口后不耐烦的摇手,有权力微澜中故意的拖延,也有规则缝隙里冰冷的刁难。每当此时,粮站清晨的风车声总会再度响起——那不仅是麦粒碰撞的声响,更是一个少年尊严被碾磨的声音。那位质检员或许早已忘记这一幕,于他不过是一次寻常的权力运用;于我,却是走出校门前深刻的人生一课。
警校毕业时,我在笔记本扉页写下:“权力再小,也不该成为为难别人的工具;位置再高,终要记得风车前的清晨。”这些年来,每办理一份证件、处理一桩纠纷、面对一次求助,这句话总会浮现。我渐渐明白:不为难他人,并非高尚的选择,而是对生存艰辛最基本的体恤。当我们在体系中获得一点位置时,最容易忘记的,往往是自己也曾站在台阶之下,仰头等待过一扇门的开启。
粮站的风车早已锈蚀在时间里,但那个清晨教会我的事,至今仍在运转:在这满是褶皱的人世间,保全他人的体面,或许就是为自己留存的最好的尊严。
|
|

 国道210过境线西安东站后面半坡过3266 人气#城市发展
国道210过境线西安东站后面半坡过3266 人气#城市发展 西安东站夜里加班装修4867 人气#城市发展
西安东站夜里加班装修4867 人气#城市发展 铁科院集团公司牵头组织实施郑西高铁运行106262 人气#城市发展
铁科院集团公司牵头组织实施郑西高铁运行106262 人气#城市发展 跨越沟沟坎坎438 人气#古城杂谈
跨越沟沟坎坎438 人气#古城杂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