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安人都注册了,还不快来?
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,没有账号?注册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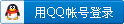

×
本帖最后由 司马君 于 2025-12-18 12:42 编辑
人过七旬,恰似立在一条望不到尽头的长廊。
来的路门虚掩着,风再也吹不进来;去的路门半合着,光也透不出去。

只剩这廊身,长得漫无边际,静得能听见自己呼吸的起伏。
时间在这里失了刻度,不再是奔涌的河,反倒成了凝滞的雾,稠得化不开。
墙上挂钟的“嘀嗒”声听久了,不似光阴流转,倒像有人持锤,一下下将“岁月”二字,钉进生命的肌理。
最磨人的是身体忽然生了“外心”。
从前它是驯顺的仆从,心念一动脚步便随;如今成了要反复商量的老邻居,固执又别扭。
想站起身,得先在心底盘算:哪条腿先着力,腰如何支撑,连手臂摆动的幅度都要斟酌。
骨头缝里像住进了吝啬的冬,丝丝寒意裹着酸意,从膝盖漫到腰肩。

桌上的药瓶渐渐排起队来,红的胶囊、白的片剂、棕的药水,像驻守边关的兵卒,日日提醒:这片曾硬朗的疆土,早已需要妥帖的照料。
夜里的睡眠是最薄的瓷,稍碰就碎。常睁着眼,看黑暗从床脚漫上来,又看窗纱上的蟹壳青,一点一点把夜稀释成灰。
白日里模糊的旧事,这时倒清晰列队:年轻时爱憎过的人面目已淡,可某年秋日梧桐叶的脉络、母亲灯下补衣的轻叹、第一次领薪水时纸币的糙感,却真切得能触碰。
原来记忆老了会挑拣,专拣这些温存细碎的片段,像怀揣着暖手的炉,焐热这漫漫长夜。
外面的世界越来越热闹,声响隔窗传来却闷闷的,像蒙着纱。
年轻人嘴里的“内卷”“元宇宙”串成串,听着像外国话。他们的影子在窗外“唰”地掠过,快得来不及看清眉眼。
有时觉得自己像件旧家具,被搬进崭新的大宅,红木的光泽与水晶灯的亮,都衬得自己格格不入——这热闹是他们的,我不过是安静的看客。
可最难熬的,不是这些,是心里那份“悬着”的慌。像秋末枝头最后一片叶,说不清眷恋什么,却颤巍巍地悬着等风来。

老友见面的次数能掰着指头算,见一次像从时光储蓄里小心取一笔,怕取尽了,就没下一次。夜里电话铃响,心先紧一下,怕听见坏消息。
后来学会了不数:不数剩几位老友,不数还能再见几次,仿佛不数,他们就永远在那里。
这份对“失去”的避讳,是岁月教的最后一课,温柔里裹着残酷。
但这条长廊从不是全然的暗,总有微光在不经意处亮着。
微光在阳台的花草上。那盆养了三年的茉莉开了三五朵白花,香气不烈,却缠缠绕绕漫过整个下午。

我蹲在盆前拂过花瓣的细绒,浇些晾好的水,剪去枯叶。不用说话,心里静得像映云的湖。
我知它喜阴怕涝,它也认得我,在我手里总长得安稳——这是彼此的托付,不声不响最是妥帖。
微光在半句老戏文里。晒太阳时忽然哼出“苏三离了洪洞县”,调子虽走了些,却勾回几十年前的黄昏——
院中的槐树下,父亲坐在石凳上,摇着蒲扇,听着收音机播出的秦腔,眯着眼,听得如痴如醉。阳光映在他鬓角的白霜上,亮得像碎银。
那一刻心里没有悲喜,只觉温温的,像抚过被岁月磨亮的木桌,纹路里都透着妥帖。
微光更在小孙女的涂鸦里。她举着画跑过来,纸上歪扭的太阳下,两个手牵手的小人一高一矮。

“爷爷,这是你和我!”脆生生的声音像小铃铛。我看着画板上不成形的线条,心里最硬的地方忽然化了,成了一汪颤悠悠的春水。
原来生命的火苗是这样传承的——我是将尽的烛芯,光暗热淡,可看着那新燃的微光,便觉自己散的烟、耗的热都值了。
再看这条长廊,心境已不同。它仍长仍静,我却不再急着去看尽头的门。
我会留意墙上的光影,看阳光从窗棂漏出,织成格子,又慢慢地移开——那是时间的脚印,轻却实在。
小区院子,大妈在跳广场舞,小孩子追逐嬉笑,树荫下几个老头下象棋,小超市那边人来人往。这些虽与我无关,却透着人间烟火的暖。
在平常的日子里,原来七秩到八秩的“熬”,从不是熬苦,是把一辈子的日子熬成一锅浓汤。

文火慢煨间,浮油沉了,渣滓清了,最后剩下那清亮的汤,说不出特别,却尝得出“就是这样了”的妥帖。
知道汤终将见底,便不再急着喝,只小口小口地品——品茉莉香,品戏文旧,品涂鸦暖,品这专属自己的最后光阴。
廊子里的光又斜移了一尺,暖融融地落在身上。
我安坐在光里,像一座安静的山,看自己的影子被岁月拉得很长,很长——却不再孤单。
2022年10月22日写于西安 图片由AI制作
| 
 2026西安城墙新春灯会官宣!4413 人气#古城杂谈
2026西安城墙新春灯会官宣!4413 人气#古城杂谈 小鼠“航天员”启程!西工大太空实验舱成功2007 人气#古城杂谈
小鼠“航天员”启程!西工大太空实验舱成功2007 人气#古城杂谈 修地铁,以前是为了卖地多挣土地出让金,现7619 人气#古城杂谈
修地铁,以前是为了卖地多挣土地出让金,现7619 人气#古城杂谈 宝鸡返回西安3130 人气#图说西安
宝鸡返回西安3130 人气#图说西安